close
180位抗戰老兵、郭柯說《二十二》、肖復興“土豆花”…【人文周刊薦讀】
導讀
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人民的偉大勝利由戰士的巨大犧牲奠基。宿遷是革命老區,新四軍在此創建淮北抗日民主根據地,是全國十九個主要根據地之一。數以萬計的宿遷子弟參軍打鬼子,許多人忠骨埋青山。自2015年起,顧園園參與宿遷晚報的抗戰老兵尋訪小組,采訪瞭180位老兵,聽他們講述烽火歲月的英雄故事。
精彩試讀
我們采訪的老兵,平均年齡89歲。70多年前,他們還是十四五歲的鄉村少年,大多不識字,甚至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但他們懂得,決不能做亡國奴。
1942年,葛聿品14歲,大哥葛聿祥、堂哥葛聿俊參加瞭彭雪楓師長的隊伍,葛聿品也要從軍。第一次報名因年紀小沒成功,他不甘心,經常給新四軍傳遞日軍據點的情報。第二年再報名,成功瞭。不久,他夜間行軍抬重機槍摔斷瞭腿,不能上陣打仗,改做地下聯絡員,負責泗洪、宿遷、新沂等根據地之間的聯絡工作。“為瞭送信,我慣常一夜來回跑幾十裡地。日本兵封村,動不動上傢裡抓共產黨,我傢因為出瞭當兵的,房子被燒瞭三次。”
葛聿品
敵後鬥爭條件艱苦,組織上給葛聿品配瞭把土槍,他因此有瞭個綽號“土機槍”。葛聿品身上挎的彈夾是用高粱稈撐起來的,隻有十來發子彈,不到關鍵時刻不舍得用。抗戰勝利前夕,葛聿品帶著遊擊隊趕往新安鎮執行任務,在一片林地遭遇一隊日軍,鬼子機槍大炮火力全開,葛聿品身邊,戰友一個個倒下。“子彈打完瞭,刀也砍豁口瞭,我們才突圍。出去時幾十個人,一晚上就剩下十幾個,太慘瞭!”老人用雙手捂住瞭臉。
采訪中,老人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我傢兄弟三人去打鬼子,隻活我一人!”
也是在1943年,也是在15歲,韓兆金參加新四軍。
韓兆金幼時,父母在蘇州工作,他在宿遷老傢讀私塾。1942年前後,日軍在蘇州、上海一帶狂轟濫炸,韓兆金的父母失業瞭,隻得回老傢,可日軍的鐵蹄已經踏上這片土地。一傢人沒有任何經濟來源,搭個窩棚住,沒有吃食,“最後,把我的小妹妹賣瞭,換瞭兩鬥糧食……”韓兆金老人痛哭失聲。
韓兆金有文化,頭腦活絡,上級安排他做偵察兵,以孩子的身份做掩護,往來各鄉鎮,搜集日軍據點的情報。
1943年下半年的一天,韓兆金拎著一籃花生,在一個叫“葉橋”的地方叫賣,忽然看到當地一個臭名昭著的漢奸。“這人平時不在傢,組織上早就想抓他,一直沒機會,當時我就想這次絕對不能讓他跑瞭。”他立即向上級匯報,同時嚴密監視漢奸動向。韓兆金和另外兩名戰友在他傢外埋伏瞭兩天兩夜,直到第三天夜裡,那漢奸出來上廁所,韓兆金和戰友悄無聲息地摸到他身後,沒費一槍一彈將他抓獲。
韓兆金
說起與日軍、漢奸周旋的故事,韓兆金時時提起戰友的名字,無限感慨:“我這些好戰友都犧牲瞭,我一次次死裡逃生,替他們看到瞭今天的美好生活。”
郭孝雲,原籍安徽,二十多歲離傢打鬼子,之後參加解放戰爭。勝利後,他帶著軍功章回老傢,父母都不在瞭。“我離傢那天,父母揮著手,叮囑我早點回來,我不敢回頭……我真後悔當時沒多看一眼。”說到這裡,老人嚎啕大哭。他的子女說,父親落戶宿遷以後再沒回過安徽,每到過年都會朝著傢鄉的方向磕三個頭。
已不識得傢人,卻不會忘記抗戰
有人說,時間可以抹去一切。但老兵的抗戰記憶不會抹去,即使老得連傢人都不認識瞭,也不會忘記民族的苦難和熱血的青春。
因為病痛,90歲的徐光彩老人記憶力衰退,常常一整天不說一句話,有時候連兒子都不認識,但他記得:“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
我們去時,徐光彩正坐在屋簷下,仰望著從簷上漏下的陽光,一聲不吭。“前幾年,他身體還不錯,哪知今年突然糊塗瞭,走路都跌跌撞撞的!”徐光彩62歲的兒子徐乃會說。
這樣的老人還能給我們講述什麼?
“您打過日本鬼子嗎?”當我第四次大聲重復這句話時,徐光彩的眼睛忽然轉動瞭一下,他大聲說:“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然後又陷入沉默。
“您在哪裡打過仗?”“打仗怕不怕?”“打仗受過傷嗎?”我反復提問,果然,“打仗”這個詞幫他在混沌中找到瞭記憶的頭緒。
“我父親去世得早,娘幾個靠要飯活命,我去當兵有吃的。”1944年,徐光彩參加瞭新四軍,到山東一帶打日本兵,他是炮兵,當過班長,用的是“六〇炮”,老人做瞭一個炮彈上膛的動作。“在濟南那次打得最慘。那是6月裡,小鬼子把我們困在一個山頭整整一個月,天天下雨,一個月沒吃過糧食,全靠吃山上的樹皮樹葉、野果子。”這一仗隻有三成戰士突圍。
徐光彩後來的講述幾乎全是碎片:“每天都行軍,一夜要跑一百裡地!”“我們武器不如人,要打遊擊戰”“冬天太冷瞭,手腳都長凍瘡”……
當我們起身要離開時,他又大聲說:“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
今年94歲的王啟,是唯一一個采訪中沒說過一句話的老兵。長期戰鬥給他造成瞭嚴重的精神創傷,1952年,王啟離開部隊,回到宿遷。
王啟的兒子王克德告訴我們,父親識字,在部隊先是做文化工作,參加過大大小小上百場戰鬥。王克德說,父親精神正常時,會講抗戰,會唱國際歌,會講犧牲的戰友,比如“日軍經常狂轟濫炸,到處都是戰友的屍體。”父親精神出問題時,要到揚州的復原軍人療養院進行康復治療。王克德說,先是爺爺送父親去,他14歲時接替爺爺,帶著父親去揚州看病。
采訪中,王克德將抗戰紀念章拿出來給大傢看,原先對周邊環境很漠然的王啟一反常態,在之後的采訪中始終專註於紀念章——或是仔細擦拭,或是掛在胸前,或是裝進口袋裡……
老兵們已屆耄耋之年,又有健康問題,采訪很困難,但總有一些申請註冊商標台中關鍵詞宛如鑰匙,能夠打開他們的記憶之門。
“嘀嘀噠噠嘀嘀……嘀嘀噠噠嘀嘀……嘀嘀噠噠嘀嘀……”許庭柱聽力極差,他的傢人告訴我,他曾是一名司號員,我就大聲哼瞭一段沖鋒號,老人馬上反應過來,說:“這是沖鋒號,我以前吹這個號最多。”
1943年7月,15歲的許庭柱,背著母親,拿上兩張煎餅,離開老傢皂河鎮,去找新四軍。他先是參加瞭區裡的獨立團,部隊安排他當司號員,送他到安徽靈璧學吹號6個月,後來編入新四軍。“我是六師一旅四十八團三營十連的。”90歲的許庭柱至今清楚地記得自己部隊的番號。
去年4月,我們去采訪94歲的牛玉陽。那時,他已經臥床兩年多,傢人說老人也許過不瞭那個夏天。
滿屋藥味,一張矮床上,牛玉陽躺在外側,92歲的老伴躺在裡側,兩位重病老人都幾乎不能說話。
在床邊,我們和牛玉陽的大兒子聊瞭起來。當提到“打鬼子”等字眼時,我們註意到老人很想說話,同事試著問:“爺爺,您打過日本鬼子沒?”“打過……”他說,還做瞭一個打槍的動作。老人聲音很小,枯瘦的雙手,動作幅度也很小……
讀《記錄》完整版請戳這裡
導讀
在1992年出版的《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最早提出瞭“知識經濟”與“知識工作者”的概念。他進一步提出,知識從“存在”變成瞭“實幹”,從個人利益變成瞭公共利益。書中,他說出瞭那句名言“知識是今天唯一有意義的資源”,這句話的力量不亞於弗蘭西斯·培根所說的“知識就是力量”。
精彩試讀
德魯克把知識的應用分成瞭三個階段:從1750年開始的第一階段,知識被應用於生產工具、生產過程和產品,從而創造瞭工業革命;從1880年開始的第二階段,知識被應用於工作,從而引發瞭生產力革命;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第三階段,知識被應用於知識本身,從而產生瞭管理革命。在德魯克看來,提供知識以找到應用現有知識創造效益的最佳方法,就是管理。
“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這一觀念後來熱門多年,但基本上沒有離開德魯克所界定的概念。後來最關鍵的補充來自日本管理學者野中鬱次郎,在1995年出版的《創造知識的企業》中,他把企業看成創造知識的組織,他從企業視角出發說,“最有價值的知識不是從別人那裡獲得的,而是我們自己創造的”。
雖然知識經濟常與信息經濟一起討論,但不管是德魯克還是很多後續探討這個議題的人,都沒有真正趕上之後25年互聯網的高速發展,我們因而看到對於知識經濟的論述很多是停留在互聯網之前。互聯網的前身阿帕網被創造出來的部分原因,是科學界為瞭進行學術知識與信息的交流。現在,互聯網已經成為全球信息與知識的存儲、交換和創造的載體,它超越瞭德魯克和野中鬱次郎所說的組織,成為知識的棲息地。
自互聯網商業化以來,人們用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來改變媒體、改變零售、改變社交、改變服務交易,人們也在設想著虛擬現實和人工智能帶來的未來,但知識似乎從未成為互聯網產業的熱點。直到2016年,突然間一個轉折點出現,知識成瞭人們關註的焦點,更準確地說,互聯網成瞭知識傳遞與交換之地。
在中國,收費知識產品與服務突然間掀起一波大浪潮。更特別的是,中國似乎成為互聯網知識產品的創新之地,部分原因是,過去在中國市場沒有足夠多和足夠好的知識產品供應,我們作為消費者也沒有形成很固定的知識產品消費習慣。在原來知識產權保護到位、內容與教育形式豐富、專業知識服務豐富的美國等市場,反而可能呈現一種所謂“發達社會的詛咒”的狀態,不易出現相關的創新。在中國,移動互聯網、移動社交和自媒體的高速發展,使得新形態的知識產品與服務更容易湧現出來。
圍繞互聯網上信息和知識的新現象出現瞭大量的新觀念,比如直接對產品的界定稱為“收費知識產品”“付費內容”;創造的新概念如“認知革命”“時間戰場”,延續和擴展之前的概念如“認知盈餘”“知識分享經濟”,或者強調投資價值的“IP”概念等。從生產者角度出發稱為“知識服務”,自稱是“知識服務商”;從平臺角度出發稱為“知識市場”;從行業角度出發稱為“知識變現”“知識付費”“內容電商”“知識電商”;從個人角度出發強調新消費與學習方式,提出“知識消費升級”“文化消費升級”等。當然,我們也可以從商業角度進行很直白的思考:知識售賣行不行?知識大規模售賣行不行?未來是否會出現大體量的互聯網知識公司?
讀《悅讀》完整版請戳這台中註冊商標流程裡
導讀
郭柯是紀錄片《三十二》《二十二》的導演;2017年8月12日《二十二》上映時,在世的老人隻剩下8人。這是他對這段拍攝經歷的“深情凝視”。
精彩試讀
2012年,我在微博上第一次看到韋紹蘭的名字,覺得她的故事非常離奇,也覺得是不錯的素材。因為此前十幾年我一直在做副導演,從事影視劇拍攝,2012年夏天,我到瞭廣西去拜訪韋紹蘭。
她曾經是我們在歷史書籍提及的慰安婦。1944年,日本陸軍第11軍包圍瞭桂林,當時韋紹蘭24歲。有一天他背著一歲的女兒在山口被日軍發現,一個日本兵舉起瞭刺刀,沒有捅她卻挑斷瞭背帶,孩子掉到地上,她沒有辦法逃跑,之後她被押上車,送往日軍據點。這輛車一路開一路抓瞭好多婦女,把她們運到瞭離新坪鎮30裡以外的炮樓裡,日本兵每天都會去強奸她們。
三個月後的一天晚上,趁著看管的日本兵打瞌睡,她背起女兒,從日本人身上慢慢邁過去逃跑瞭。她順著小路走到天亮又走到快天黑,然後和孩子縮在一個老奶奶傢的稻草裡度過瞭離開日本據點的第一晚。第二天又走到天黑,終於回到自己傢裡。當時她的丈夫在吃飯,看見她就說:“你回來瞭?我還以為你不知道回來瞭。”韋紹蘭當時就哭瞭,反而是她的婆婆勸她,說先給阿妹煮點粥吃,吃完瞭給她洗個澡。丈夫恨她罵她,說她出去學壞瞭。婆婆說她不是學壞瞭,她是在山頭被日本人拿走的。鄰居也說,幸虧她乖(當地人把機靈稱作“乖”)自己跑出來,有的人想跑都跑不出來。
韋紹蘭是11月份跑回去的,大概是因為營養不良,12月份她的女兒死掉瞭。又過瞭一個月,她發現自己懷孕瞭,懷的日本人的孩子。她就想死,喝農藥,被鄰居救回來。婆婆還是勸她,不管男孩女孩都得生下來,萬一你以後沒生育能力怎麼辦?1945年,她生下那個孩子,取名羅善學。
羅善學告訴我,他從小受到異樣的眼光看待,至今沒結婚。韋紹蘭現在靠低保生活,一個月90塊錢,每三個月到鎮上領一次。她吃的最多的就是白菜,因為白菜便宜。在見她們之前,我心裡是有一些預判和想象的,但是這個老人身上終究有些東西是我沒想到的。有一次問母子倆,你們對將來怎麼看?韋紹蘭回答,說我還沒活夠,這個世界紅紅火火的,我要留著這條命來看。我當時就想這個老人她為什麼心裡會那麼樂觀?我們聊天時她經常走神,所以我聽她說過這麼幾句話:天下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憂愁自己解,自流眼淚自抹幹。這可能是當地的俗語,但從她嘴裡念出來,仿佛是說自己的人生。
讀《百傢》完整版請戳這裡
導讀
土豆花是什麼?你看過嗎?本期《新潮》邀請到著名作傢肖復興,帶你去看看記憶中的北大荒,記憶中的土豆花。
精彩試讀
肖復興
在北大荒,我們隊的最西頭是菜地。那時,各傢不興自留地,全隊人都得靠這片菜地吃菜。菜地裡種得最多的是土豆,秋收的台灣商標註冊時候,各傢來人,一麻袋一麻袋把土豆扛回傢,放進地窖。土豆是東北人的看傢菜,一冬一春下飯大部分靠著它。
土豆夏天開花,花不顯眼,要說好看,趕不上扁豆花和倭瓜花。扁豆花比土豆花鮮艷,紫瑩瑩的,一串一串,夢一般的小星星,隨風搖曳,很優雅的樣子。倭瓜花明晃晃的,顏色本來就打眼,花盤又大,很是招搖,常有蜜蜂在上面飛,嗡嗡嗡嗡,很開心地為花們唱歌。
和它們比,土豆花一下子就被擠到下風頭。土豆種在菜地的最邊上,外面就是一片荒原。在半人高的萋萋荒草面前,土豆花顯得更加弱小更加微不足道。剛來北大荒那幾年,夏天土豆開花的時候,我常去菜地給知青食堂摘菜,或者偷吃西紅柿黃瓜,但從沒註意到土豆花,還以為土豆不開花。
第一次看到土豆花,是來北大荒三年後的夏天,我在隊上的小學校當老師。
小學校除瞭校長就我一個老師,一年級到六年級的所有課程,都是校長和我教,校長負責低年級,我負責高年級。三個高年級的學生,擠在一間屋裡上課,按下葫蘆起瞭瓢,鬧成一團。我算是個負責的老師,很喜歡這群活潑可愛的孩子。有一天發現五年級一個女孩子連續好幾天沒來上課,很是惦記,一問,學生七嘴八舌嚷嚷起來:她爸不讓她上學瞭!
為什麼?最主要的原因是孩子多,生活困難,就讓女孩子輟學,早早幹活,分擔傢裡的困難。那時候,我心裡充滿自以為是的悲天憫人的情感和年輕湧動的激情,希望說服女孩的父母讓她多上幾年學,便在沒課的一天下午去瞭她傢。
她是我們隊管菜地的老李頭的大女兒,她傢就在菜地最邊上,在荒原上開出一片地,用拉禾辮蓋起的茅草房。那天下午,女孩子在菜地裡幫爸爸幹活,大老遠看見我,高聲沖我叫“肖老師”,跑瞭過來。見她身上粘著草,腳上裹著泥,破草帽下的臉上掛滿汗珠,我心想,這樣的活兒,不應該是她這樣小的孩子幹的。
老李頭不善言辭,他很有耐心地聽我把話砸薑磨蒜地說完,翻來覆去就一句:我也是沒有辦法呀!傢裡孩子多,她媽媽又有病。我也是沒有辦法呀!女孩子眼巴巴地望望我,又望望爸爸。我一肚子的話都倒幹凈瞭,不知道再說什麼好。農民的經濟壓力,也許不是我們知青能夠體會的,在沉重的生活面前,同情心打不起一點分量。
我心裡充滿挫折感,一聲不吭地走出菜地。女孩子一直在後面跟著,送我,我不敢回頭看她。她上學晚,那一年大概十三四歲,很懂事。分手的時候,倒是她安慰我:沒關系的,肖老師!在菜地裡幹活也挺好,您看,這些土豆花挺好看的呢!
我這才發現,剛才走進走出的是土豆地,她身後那片土豆正在開花。我也才發現,她的破草帽上,圍著一圈土豆花編織的花環。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土豆花,那麼小,一不留神就會被忽略。花是淡藍色的,一朵朵簇擁在一起,一串串的麥穗一樣,確實挺好看,但在陽光炙烤下,褪瞭色般,有些暗淡。
從那時起,土豆花總讓我心生憂鬱,也總忘不瞭。離開北大荒調回北京的那一年夏天,我特意邀朋友到隊上這片土豆地裡拍照留念,但是,土豆花實在太小瞭,照片上根本看不清。
前幾年夏天回到北大荒,過七星河,直奔插隊所在的生產隊,一眼就看見隊上那一片土豆地裡正在開花。幾十年過去瞭,真讓人覺得時光在這裡定格。
讀《新潮》完整版請戳這裡
導讀
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人民的偉大勝利由戰士的巨大犧牲奠基。宿遷是革命老區,新四軍在此創建淮北抗日民主根據地,是全國十九個主要根據地之一。數以萬計的宿遷子弟參軍打鬼子,許多人忠骨埋青山。自2015年起,顧園園參與宿遷晚報的抗戰老兵尋訪小組,采訪瞭180位老兵,聽他們講述烽火歲月的英雄故事。
精彩試讀
我們采訪的老兵,平均年齡89歲。70多年前,他們還是十四五歲的鄉村少年,大多不識字,甚至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但他們懂得,決不能做亡國奴。
1942年,葛聿品14歲,大哥葛聿祥、堂哥葛聿俊參加瞭彭雪楓師長的隊伍,葛聿品也要從軍。第一次報名因年紀小沒成功,他不甘心,經常給新四軍傳遞日軍據點的情報。第二年再報名,成功瞭。不久,他夜間行軍抬重機槍摔斷瞭腿,不能上陣打仗,改做地下聯絡員,負責泗洪、宿遷、新沂等根據地之間的聯絡工作。“為瞭送信,我慣常一夜來回跑幾十裡地。日本兵封村,動不動上傢裡抓共產黨,我傢因為出瞭當兵的,房子被燒瞭三次。”
葛聿品
敵後鬥爭條件艱苦,組織上給葛聿品配瞭把土槍,他因此有瞭個綽號“土機槍”。葛聿品身上挎的彈夾是用高粱稈撐起來的,隻有十來發子彈,不到關鍵時刻不舍得用。抗戰勝利前夕,葛聿品帶著遊擊隊趕往新安鎮執行任務,在一片林地遭遇一隊日軍,鬼子機槍大炮火力全開,葛聿品身邊,戰友一個個倒下。“子彈打完瞭,刀也砍豁口瞭,我們才突圍。出去時幾十個人,一晚上就剩下十幾個,太慘瞭!”老人用雙手捂住瞭臉。
采訪中,老人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我傢兄弟三人去打鬼子,隻活我一人!”
也是在1943年,也是在15歲,韓兆金參加新四軍。
韓兆金幼時,父母在蘇州工作,他在宿遷老傢讀私塾。1942年前後,日軍在蘇州、上海一帶狂轟濫炸,韓兆金的父母失業瞭,隻得回老傢,可日軍的鐵蹄已經踏上這片土地。一傢人沒有任何經濟來源,搭個窩棚住,沒有吃食,“最後,把我的小妹妹賣瞭,換瞭兩鬥糧食……”韓兆金老人痛哭失聲。
韓兆金有文化,頭腦活絡,上級安排他做偵察兵,以孩子的身份做掩護,往來各鄉鎮,搜集日軍據點的情報。
1943年下半年的一天,韓兆金拎著一籃花生,在一個叫“葉橋”的地方叫賣,忽然看到當地一個臭名昭著的漢奸。“這人平時不在傢,組織上早就想抓他,一直沒機會,當時我就想這次絕對不能讓他跑瞭。”他立即向上級匯報,同時嚴密監視漢奸動向。韓兆金和另外兩名戰友在他傢外埋伏瞭兩天兩夜,直到第三天夜裡,那漢奸出來上廁所,韓兆金和戰友悄無聲息地摸到他身後,沒費一槍一彈將他抓獲。
韓兆金
說起與日軍、漢奸周旋的故事,韓兆金時時提起戰友的名字,無限感慨:“我這些好戰友都犧牲瞭,我一次次死裡逃生,替他們看到瞭今天的美好生活。”
郭孝雲,原籍安徽,二十多歲離傢打鬼子,之後參加解放戰爭。勝利後,他帶著軍功章回老傢,父母都不在瞭。“我離傢那天,父母揮著手,叮囑我早點回來,我不敢回頭……我真後悔當時沒多看一眼。”說到這裡,老人嚎啕大哭。他的子女說,父親落戶宿遷以後再沒回過安徽,每到過年都會朝著傢鄉的方向磕三個頭。
已不識得傢人,卻不會忘記抗戰
有人說,時間可以抹去一切。但老兵的抗戰記憶不會抹去,即使老得連傢人都不認識瞭,也不會忘記民族的苦難和熱血的青春。
因為病痛,90歲的徐光彩老人記憶力衰退,常常一整天不說一句話,有時候連兒子都不認識,但他記得:“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
我們去時,徐光彩正坐在屋簷下,仰望著從簷上漏下的陽光,一聲不吭。“前幾年,他身體還不錯,哪知今年突然糊塗瞭,走路都跌跌撞撞的!”徐光彩62歲的兒子徐乃會說。
這樣的老人還能給我們講述什麼?
“您打過日本鬼子嗎?”當我第四次大聲重復這句話時,徐光彩的眼睛忽然轉動瞭一下,他大聲說:“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然後又陷入沉默。
“您在哪裡打過仗?”“打仗怕不怕?”“打仗受過傷嗎?”我反復提問,果然,“打仗”這個詞幫他在混沌中找到瞭記憶的頭緒。
“我父親去世得早,娘幾個靠要飯活命,我去當兵有吃的。”1944年,徐光彩參加瞭新四軍,到山東一帶打日本兵,他是炮兵,當過班長,用的是“六〇炮”,老人做瞭一個炮彈上膛的動作。“在濟南那次打得最慘。那是6月裡,小鬼子把我們困在一個山頭整整一個月,天天下雨,一個月沒吃過糧食,全靠吃山上的樹皮樹葉、野果子。”這一仗隻有三成戰士突圍。
徐光彩後來的講述幾乎全是碎片:“每天都行軍,一夜要跑一百裡地!”“我們武器不如人,要打遊擊戰”“冬天太冷瞭,手腳都長凍瘡”……
當我們起身要離開時,他又大聲說:“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
今年94歲的王啟,是唯一一個采訪中沒說過一句話的老兵。長期戰鬥給他造成瞭嚴重的精神創傷,1952年,王啟離開部隊,回到宿遷。
王啟的兒子王克德告訴我們,父親識字,在部隊先是做文化工作,參加過大大小小上百場戰鬥。王克德說,父親精神正常時,會講抗戰,會唱國際歌,會講犧牲的戰友,比如“日軍經常狂轟濫炸,到處都是戰友的屍體。”父親精神出問題時,要到揚州的復原軍人療養院進行康復治療。王克德說,先是爺爺送父親去,他14歲時接替爺爺,帶著父親去揚州看病。
采訪中,王克德將抗戰紀念章拿出來給大傢看,原先對周邊環境很漠然的王啟一反常態,在之後的采訪中始終專註於紀念章——或是仔細擦拭,或是掛在胸前,或是裝進口袋裡……
老兵們已屆耄耋之年,又有健康問題,采訪很困難,但總有一些申請註冊商標台中關鍵詞宛如鑰匙,能夠打開他們的記憶之門。
“嘀嘀噠噠嘀嘀……嘀嘀噠噠嘀嘀……嘀嘀噠噠嘀嘀……”許庭柱聽力極差,他的傢人告訴我,他曾是一名司號員,我就大聲哼瞭一段沖鋒號,老人馬上反應過來,說:“這是沖鋒號,我以前吹這個號最多。”
1943年7月,15歲的許庭柱,背著母親,拿上兩張煎餅,離開老傢皂河鎮,去找新四軍。他先是參加瞭區裡的獨立團,部隊安排他當司號員,送他到安徽靈璧學吹號6個月,後來編入新四軍。“我是六師一旅四十八團三營十連的。”90歲的許庭柱至今清楚地記得自己部隊的番號。
去年4月,我們去采訪94歲的牛玉陽。那時,他已經臥床兩年多,傢人說老人也許過不瞭那個夏天。
滿屋藥味,一張矮床上,牛玉陽躺在外側,92歲的老伴躺在裡側,兩位重病老人都幾乎不能說話。
在床邊,我們和牛玉陽的大兒子聊瞭起來。當提到“打鬼子”等字眼時,我們註意到老人很想說話,同事試著問:“爺爺,您打過日本鬼子沒?”“打過……”他說,還做瞭一個打槍的動作。老人聲音很小,枯瘦的雙手,動作幅度也很小……
讀《記錄》完整版請戳這裡
導讀
在1992年出版的《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最早提出瞭“知識經濟”與“知識工作者”的概念。他進一步提出,知識從“存在”變成瞭“實幹”,從個人利益變成瞭公共利益。書中,他說出瞭那句名言“知識是今天唯一有意義的資源”,這句話的力量不亞於弗蘭西斯·培根所說的“知識就是力量”。
精彩試讀
德魯克把知識的應用分成瞭三個階段:從1750年開始的第一階段,知識被應用於生產工具、生產過程和產品,從而創造瞭工業革命;從1880年開始的第二階段,知識被應用於工作,從而引發瞭生產力革命;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第三階段,知識被應用於知識本身,從而產生瞭管理革命。在德魯克看來,提供知識以找到應用現有知識創造效益的最佳方法,就是管理。
“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這一觀念後來熱門多年,但基本上沒有離開德魯克所界定的概念。後來最關鍵的補充來自日本管理學者野中鬱次郎,在1995年出版的《創造知識的企業》中,他把企業看成創造知識的組織,他從企業視角出發說,“最有價值的知識不是從別人那裡獲得的,而是我們自己創造的”。
雖然知識經濟常與信息經濟一起討論,但不管是德魯克還是很多後續探討這個議題的人,都沒有真正趕上之後25年互聯網的高速發展,我們因而看到對於知識經濟的論述很多是停留在互聯網之前。互聯網的前身阿帕網被創造出來的部分原因,是科學界為瞭進行學術知識與信息的交流。現在,互聯網已經成為全球信息與知識的存儲、交換和創造的載體,它超越瞭德魯克和野中鬱次郎所說的組織,成為知識的棲息地。
自互聯網商業化以來,人們用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來改變媒體、改變零售、改變社交、改變服務交易,人們也在設想著虛擬現實和人工智能帶來的未來,但知識似乎從未成為互聯網產業的熱點。直到2016年,突然間一個轉折點出現,知識成瞭人們關註的焦點,更準確地說,互聯網成瞭知識傳遞與交換之地。
在中國,收費知識產品與服務突然間掀起一波大浪潮。更特別的是,中國似乎成為互聯網知識產品的創新之地,部分原因是,過去在中國市場沒有足夠多和足夠好的知識產品供應,我們作為消費者也沒有形成很固定的知識產品消費習慣。在原來知識產權保護到位、內容與教育形式豐富、專業知識服務豐富的美國等市場,反而可能呈現一種所謂“發達社會的詛咒”的狀態,不易出現相關的創新。在中國,移動互聯網、移動社交和自媒體的高速發展,使得新形態的知識產品與服務更容易湧現出來。
圍繞互聯網上信息和知識的新現象出現瞭大量的新觀念,比如直接對產品的界定稱為“收費知識產品”“付費內容”;創造的新概念如“認知革命”“時間戰場”,延續和擴展之前的概念如“認知盈餘”“知識分享經濟”,或者強調投資價值的“IP”概念等。從生產者角度出發稱為“知識服務”,自稱是“知識服務商”;從平臺角度出發稱為“知識市場”;從行業角度出發稱為“知識變現”“知識付費”“內容電商”“知識電商”;從個人角度出發強調新消費與學習方式,提出“知識消費升級”“文化消費升級”等。當然,我們也可以從商業角度進行很直白的思考:知識售賣行不行?知識大規模售賣行不行?未來是否會出現大體量的互聯網知識公司?
讀《悅讀》完整版請戳這台中註冊商標流程裡
導讀
郭柯是紀錄片《三十二》《二十二》的導演;2017年8月12日《二十二》上映時,在世的老人隻剩下8人。這是他對這段拍攝經歷的“深情凝視”。
精彩試讀
2012年,我在微博上第一次看到韋紹蘭的名字,覺得她的故事非常離奇,也覺得是不錯的素材。因為此前十幾年我一直在做副導演,從事影視劇拍攝,2012年夏天,我到瞭廣西去拜訪韋紹蘭。
她曾經是我們在歷史書籍提及的慰安婦。1944年,日本陸軍第11軍包圍瞭桂林,當時韋紹蘭24歲。有一天他背著一歲的女兒在山口被日軍發現,一個日本兵舉起瞭刺刀,沒有捅她卻挑斷瞭背帶,孩子掉到地上,她沒有辦法逃跑,之後她被押上車,送往日軍據點。這輛車一路開一路抓瞭好多婦女,把她們運到瞭離新坪鎮30裡以外的炮樓裡,日本兵每天都會去強奸她們。
三個月後的一天晚上,趁著看管的日本兵打瞌睡,她背起女兒,從日本人身上慢慢邁過去逃跑瞭。她順著小路走到天亮又走到快天黑,然後和孩子縮在一個老奶奶傢的稻草裡度過瞭離開日本據點的第一晚。第二天又走到天黑,終於回到自己傢裡。當時她的丈夫在吃飯,看見她就說:“你回來瞭?我還以為你不知道回來瞭。”韋紹蘭當時就哭瞭,反而是她的婆婆勸她,說先給阿妹煮點粥吃,吃完瞭給她洗個澡。丈夫恨她罵她,說她出去學壞瞭。婆婆說她不是學壞瞭,她是在山頭被日本人拿走的。鄰居也說,幸虧她乖(當地人把機靈稱作“乖”)自己跑出來,有的人想跑都跑不出來。
韋紹蘭是11月份跑回去的,大概是因為營養不良,12月份她的女兒死掉瞭。又過瞭一個月,她發現自己懷孕瞭,懷的日本人的孩子。她就想死,喝農藥,被鄰居救回來。婆婆還是勸她,不管男孩女孩都得生下來,萬一你以後沒生育能力怎麼辦?1945年,她生下那個孩子,取名羅善學。
羅善學告訴我,他從小受到異樣的眼光看待,至今沒結婚。韋紹蘭現在靠低保生活,一個月90塊錢,每三個月到鎮上領一次。她吃的最多的就是白菜,因為白菜便宜。在見她們之前,我心裡是有一些預判和想象的,但是這個老人身上終究有些東西是我沒想到的。有一次問母子倆,你們對將來怎麼看?韋紹蘭回答,說我還沒活夠,這個世界紅紅火火的,我要留著這條命來看。我當時就想這個老人她為什麼心裡會那麼樂觀?我們聊天時她經常走神,所以我聽她說過這麼幾句話:天下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憂愁自己解,自流眼淚自抹幹。這可能是當地的俗語,但從她嘴裡念出來,仿佛是說自己的人生。
讀《百傢》完整版請戳這裡
導讀
土豆花是什麼?你看過嗎?本期《新潮》邀請到著名作傢肖復興,帶你去看看記憶中的北大荒,記憶中的土豆花。
精彩試讀
肖復興
在北大荒,我們隊的最西頭是菜地。那時,各傢不興自留地,全隊人都得靠這片菜地吃菜。菜地裡種得最多的是土豆,秋收的台灣商標註冊時候,各傢來人,一麻袋一麻袋把土豆扛回傢,放進地窖。土豆是東北人的看傢菜,一冬一春下飯大部分靠著它。
土豆夏天開花,花不顯眼,要說好看,趕不上扁豆花和倭瓜花。扁豆花比土豆花鮮艷,紫瑩瑩的,一串一串,夢一般的小星星,隨風搖曳,很優雅的樣子。倭瓜花明晃晃的,顏色本來就打眼,花盤又大,很是招搖,常有蜜蜂在上面飛,嗡嗡嗡嗡,很開心地為花們唱歌。
和它們比,土豆花一下子就被擠到下風頭。土豆種在菜地的最邊上,外面就是一片荒原。在半人高的萋萋荒草面前,土豆花顯得更加弱小更加微不足道。剛來北大荒那幾年,夏天土豆開花的時候,我常去菜地給知青食堂摘菜,或者偷吃西紅柿黃瓜,但從沒註意到土豆花,還以為土豆不開花。
第一次看到土豆花,是來北大荒三年後的夏天,我在隊上的小學校當老師。
小學校除瞭校長就我一個老師,一年級到六年級的所有課程,都是校長和我教,校長負責低年級,我負責高年級。三個高年級的學生,擠在一間屋裡上課,按下葫蘆起瞭瓢,鬧成一團。我算是個負責的老師,很喜歡這群活潑可愛的孩子。有一天發現五年級一個女孩子連續好幾天沒來上課,很是惦記,一問,學生七嘴八舌嚷嚷起來:她爸不讓她上學瞭!
為什麼?最主要的原因是孩子多,生活困難,就讓女孩子輟學,早早幹活,分擔傢裡的困難。那時候,我心裡充滿自以為是的悲天憫人的情感和年輕湧動的激情,希望說服女孩的父母讓她多上幾年學,便在沒課的一天下午去瞭她傢。
她是我們隊管菜地的老李頭的大女兒,她傢就在菜地最邊上,在荒原上開出一片地,用拉禾辮蓋起的茅草房。那天下午,女孩子在菜地裡幫爸爸幹活,大老遠看見我,高聲沖我叫“肖老師”,跑瞭過來。見她身上粘著草,腳上裹著泥,破草帽下的臉上掛滿汗珠,我心想,這樣的活兒,不應該是她這樣小的孩子幹的。
老李頭不善言辭,他很有耐心地聽我把話砸薑磨蒜地說完,翻來覆去就一句:我也是沒有辦法呀!傢裡孩子多,她媽媽又有病。我也是沒有辦法呀!女孩子眼巴巴地望望我,又望望爸爸。我一肚子的話都倒幹凈瞭,不知道再說什麼好。農民的經濟壓力,也許不是我們知青能夠體會的,在沉重的生活面前,同情心打不起一點分量。
我心裡充滿挫折感,一聲不吭地走出菜地。女孩子一直在後面跟著,送我,我不敢回頭看她。她上學晚,那一年大概十三四歲,很懂事。分手的時候,倒是她安慰我:沒關系的,肖老師!在菜地裡幹活也挺好,您看,這些土豆花挺好看的呢!
我這才發現,剛才走進走出的是土豆地,她身後那片土豆正在開花。我也才發現,她的破草帽上,圍著一圈土豆花編織的花環。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土豆花,那麼小,一不留神就會被忽略。花是淡藍色的,一朵朵簇擁在一起,一串串的麥穗一樣,確實挺好看,但在陽光炙烤下,褪瞭色般,有些暗淡。
從那時起,土豆花總讓我心生憂鬱,也總忘不瞭。離開北大荒調回北京的那一年夏天,我特意邀朋友到隊上這片土豆地裡拍照留念,但是,土豆花實在太小瞭,照片上根本看不清。
前幾年夏天回到北大荒,過七星河,直奔插隊所在的生產隊,一眼就看見隊上那一片土豆地裡正在開花。幾十年過去瞭,真讓人覺得時光在這裡定格。
讀《新潮》完整版請戳這裡
AUGI SPORTS|重機車靴|重機車靴推薦|重機專用車靴|重機防摔鞋|重機防摔鞋推薦|重機防摔鞋
AUGI SPORTS|augisports|racing boots|urban boots|motorcycle boots
文章標籤
全站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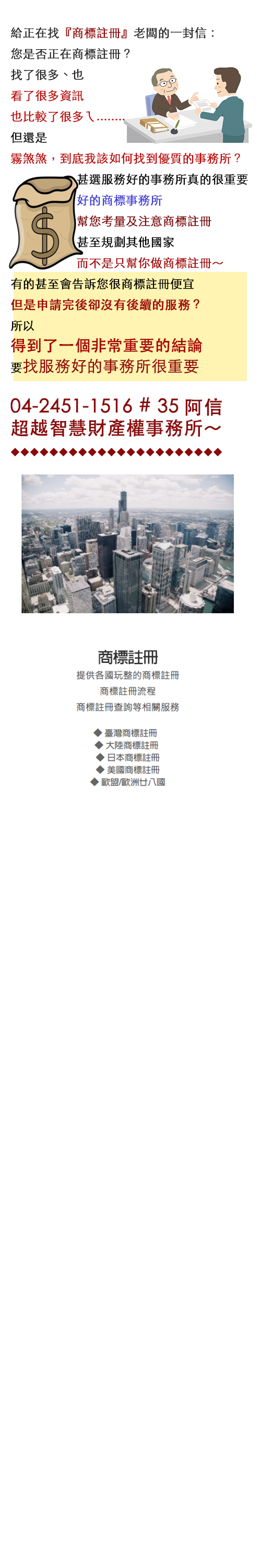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